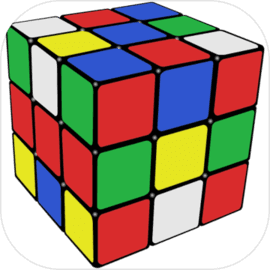关于月亮的散文一:月亮之下
在月亮的下面,你知道我在哪里吗?在草原还是在山岗?在峡谷还是在山顶。在大海还是在沙漠。不要多问反正我在月亮之下。有缘千里来相会,只要有缘,必将相会。如若无缘即使对面也会错过。有时需要等待,等待也是一种策略。
有时必需奋起直追,一分一秒都会错过。刻不容缓分秒必争宁肯超过也不愿错过。
月亮走,我也走,走来走去还在月亮下头。心不动人难走。
月亮不指示方向,错就错在找错参照物。月亮之下广袤无边无际,何处是停留之地。何处是心安顿之所。事已至此先找一棵大树,让心寄居。虽然不能避雨,但是可以遮挡阳光。可以渴饮甘露。
在山顶树木也不能辨别方向,走得越快离得越远,焦灼的心,迷失的路,在脚下吗?
在沙漠朦朦原野,不要说树,就是草也找不到一株,我拿什么救命?对着月亮喊,月亮不回答,对着星星喊,星星眨眨眼,轻风不说话。干枯的沙子不动也不说。只有沙蜘蛛在沙子里愉快的生活,一点也不觉得苦。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不是堕落,只是选择了另一种坚强。宁弯不折委曲求全是生命的另一首歌。为什么非要宁折不弯呢,挫折只是暂时的,困难过去,天宽地宽。折了还拿什么去拼搏明天。困难面前低低头不羞人,不受辱,只为每天更强大的站立。
关于月亮的散文二:故乡的月亮
好温馨,略带一缕忧伤,总在夜阑人静,晖洒如水,孤寥沉沉时,你就悄悄的爬满草坡,漫入西窗,潜入我的紫梦,诱出呢喃呓语,携着柔眼星宿,披着袅袅霭雾,载着幽幽花香,轻抚我的梦中甜蜜,轻吻我无依的眼泪,朦胧中我感怀深深,盈眶漫溢,我把一生的倦恋都渗放在你的长思中——难忘的故乡月!
你的银晖有多远,母亲的牵挂就有多远,你的轻抚有多柔,母亲的慈爱就有多深,你用温情陪伴我一生,母亲用掌心就托住我长长的岁月,真到斑驳的双鬓染上澄色夕阳有了西下的意思。
当紫暮降临时,我载着思念穿过云层,借着星宿的柔光回到你轻洒如水,土气浓浓,依然温馨弥漫的老院坝,再次沐浴在你淡淡的清晖里,我用遥远的呼吸轻抚门前那棵老树,用泪眼重湿门前那生满苔藓的石梯,清亮的石板坡就再现我深情而倦恋的足迹,
如今,岁月缩短,心思沉沉,步履蹒跚,思念你的梦境就更是清晰频频。
时有举头,拥抱你——遥远又亲近的家乡月犹如拥抱童年的月亮船,让许多许多不经意就失去的憧憬重新载回到我温馨的梦境。
关于月亮的散文三:寮角的月亮
寮屋,早年放稻草。
田间晒干的稻草,一捆捆挑回。这轻挑得多,满得快。寮内满了靠外墙堆着。一些秕谷也堆旁边。最后门一关锁一扣,寮屋安安静静。
入冬,它才醒来。
搬开外墙稻草,地上稀疏谷子,鸡鸭们喜欢,一出笼就往里钻,这让孩子们轻松。心眼多的孩子弄来火点,往秕谷上一扔,火舌一舔,谷堆在淡霉和薄烟里一脸乌黑。几双小手摊火前,渐渐柔软。火堆中有沉闷响,偶尔窜出几粒爆米花。雪白的爆米花,火一卷,焦黄;烟一熏,暗黑;眨几眼,着火。爆米花香酥脆,即便夜里,孩子们也无法抵挡其诱惑。凡烧秕谷总持竹竿,往里一挑,一片火星,一股烟尘,一串噼呖啪啦,一批爆米花蹦出来,星子般。小手快速撮着,直塞嘴里。最后惹得两手瞅乌,一嘴灰黑。火屑和烟灰飘过寮顶,隐匿在空中。天,晾在夜里,宽大幽蓝。洗天的风在山谷,在溪沿,在枝头,徘徊着,不歇息。月,一声不语,慢慢前行。她冷吗?冷的话用什么烤暖?星子是她的爆米花,满天都是,没人争,她是拣不完的,除非雨浇湿了天火。有朝一日我会骑上天马,拣一麻袋爆米花,倒笸篮里,慢慢吃,直到缺牙。
月,喜静的,人睡了,她起床。人干活她才睡,会吵她吗?想必她在夜里也打瞌睡。
我在寮屋火堆边常瞌睡,尤其在迎新人的'夜里。
房里有人结婚,少不了在寮角生堆火,小的便围着,懒得睡。老的交代女方娘家来人,房里要去接灯,并指定几个男孩,女孩没份,大概“灯”通“丁”。接灯的报酬每人两角钱红包。没去的围在火前,等新人撒糖果。大人说着新人如何标致,月上村口山头时出门。等到大家不愿说话,便轮流到村口,目勾勾盼新人来。我想新人一定是乘弯月船而来,星子在船头点灯。船将新人送到村口后,躲在云端偷看。月船上的人白净,着丝绸,系彩带,穿高鞘,步子轻飘。新人带来的糖果,我捡最多,每个口袋满满的。迷糊中不知谁说来了,隐隐有锣鼓和唢呐响,节奏清晰,渐渐飘来,几点红灯,慢慢摇来。新人穿红衫着红鞋,头遮红巾,在红伞簇拥下,跳过火炉,踩着簸箕,跨入门坎,酥手一扬,丝帕一抖,花生、红枣、桔饼、糖果,一地闪,人群蜂拥而上。人散我坐在大门的石础上,打量手里的几只糖果。寮顶的月脸白牙靓,正对我笑。哪天月亮出嫁,想必也是一身红妆。
田要追基肥,稻草就回田里。不放稻草的寮屋,关猪。里头暗夜里,油灯一映,人影肥大,挡暗一扇墙,加上寮外牛脚敲着地鼓,多少让人胆小。母亲卸下寮顶两块青瓦,换上玻璃的。透过玻璃瓦的月光,象从电影镜头出来,冒着薄气,照在粉嘟嘟的小猪身上,照得母猪鼾声阵阵,照得小猪吃奶吱吱响。月不西落多好!月不落,太阳起来,它们打架,没人劝,也不好。
寮外排粪沟。沟旁种南瓜、葫芦、花蝴豆。
南瓜苗,藤粗蔓密,叶碧绿,毛绒绒,花开叶间,翡翠镶金。葫芦白花圆叶,没那么率意,也没那么金贵。花蝴豆藤大片垂下,帘子般,白花和红豆,养眼。白天蝴蝶来,蜻蜓也来。蝴蝶忽上忽下,女孩喜欢,但它们的羽易碎,粉有毒,手粘后起泡。倒是青蜻蜓趴在叶沿,呆呆的,孩子们伸出拇指和食指,小心翼翼,对准其尾,快速一捏。抓住了折去透明翅膀,任其在地上打转,稍疏忽,便被鸡啄去。
一些清早,红蜻蜓被着露水,枕着藤,守着瓜。红蜻蜓头大,尾短,身小,平时多在水塘。水塘能让它们安静欣赏自己,没人打扰。邻村一女孩头系红绸,身着红裙,在水塘边,低头捶衣洗菜,若红蜻蜓。她的脸塘里的月光般,一闪闪的。
这时的南瓜,圆鼓金灿,枕在瓦上,在吆喝声上,经梯子一步步走下来,走进寮屋;悬于椽角的葫芦,放在地上,被锯子对中拉着,稍不小心,崩去一块,一声轻叹,扔作猪食。对开的挖瓤去子,晾干成勺。
孩子们一高兴,坐在寮顶,不肯下来。
老的说,呆在寮顶,仙女会来发月饼。
仙女发的饼多大?
月光般。
月光大的饼,咬得动吗?
用锯,锯葫芦般,每人一块。
我不要月饼,要月光。我把它挂在屋檐,照亮家里每个角落。揣在身上再夜再远不迷路。
月光发给你,那天上还有吗?
仙女印饼般,再做一只。不然我拗一块也行。
拗了不就坏了嘛?
它不是会长回去嘛。
要不我舀几瓢。
舀来做嘛?放哪?
我能喝,放在寮里慢慢喝,然后浑身发光。
等着,等着。月上山过中天,从没见仙女来发月饼。
母亲一人在家,没养猪了,寮屋放化肥锄头水桶,也放地瓜芋头大薯。不待上春挂在枕梁上的大薯,吐出粒芽,或绿或粉,或黄或白,寮内,恍若星空。天一暖嫩芽伸舌,再几出雨,芽便探到椽底,想揭开玻璃瓦,上屋顶,看月去。此时的月有薄绒毛,风,擦不净。我想这个季节她不捡爆米花,天上稻田正绿。
前年,寮檐参差,老妇的牙般。打开旧门寮顶椽子烂了一半。举头直对天。梁上的蕨草根枝茂繁;墙上的雨痕,皱纹缜密;墙脚的青苔,青春年少。是夜有月我再推开寮门,静静站在里头。叠在寮顶二十年的月光,从梁中淋下,把我压在脚跟。
寮屋,终究会平的。那时我会在秋水边,骑着天马,捡着爆米花,去看红月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