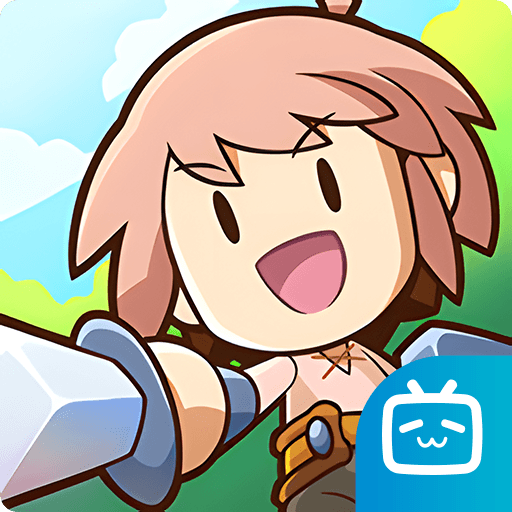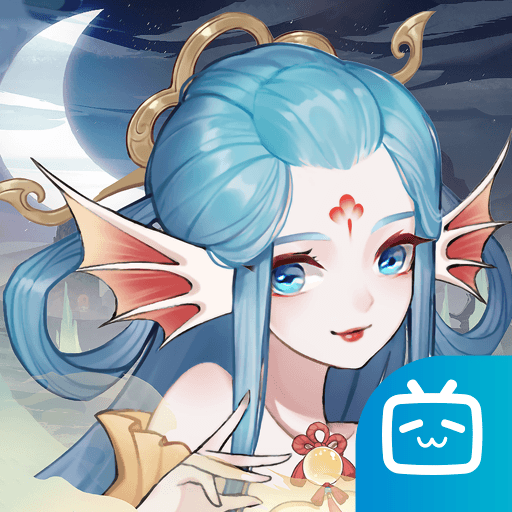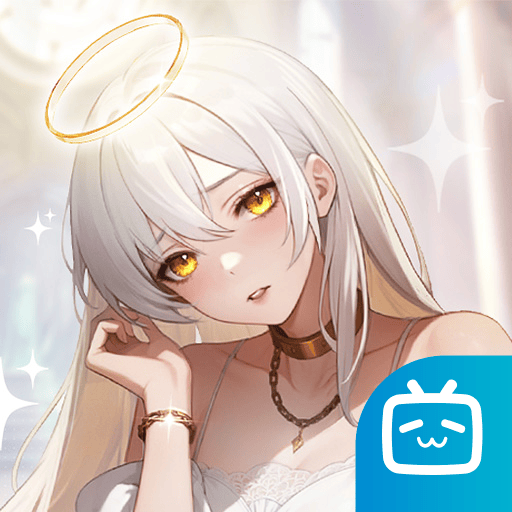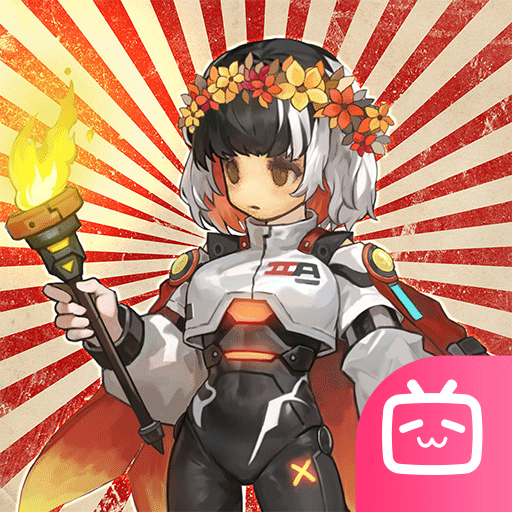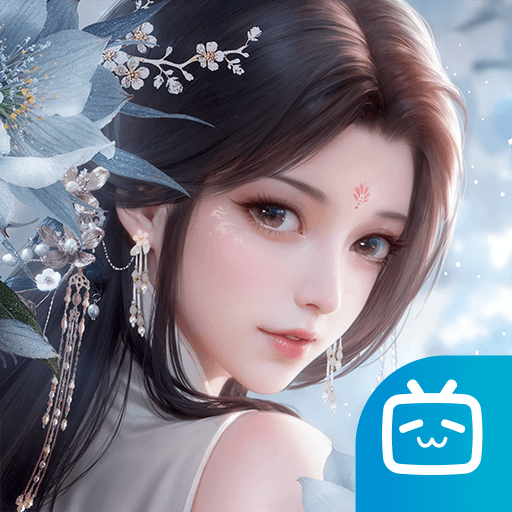你离开在风起的清晨眼神若水雾般的仲夏
身披着腥红的秋晚怀念貌若冬梨花
如果可以我想把最美的四季寄给你。
鬼节刚过,空气随着季节的变换,也变得清爽。家里大扫除收拾出一些做鞋垫用的小布块,盛着它们的是用粉红手绢缝制的简易的小包,布块里还夹着一张白纸,上面一排一排画着铅笔划过的痕迹,有的是一道横,有的是两道横,有的三道,四道……
收拾老房子总会有探险的感觉,那些破旧的东西,总会带来一些陌生的熟悉感,用手拍去尘土,记忆也随之而来。
书架上有个盒子,外面的表面都有些裂开了,里面有些我的小学初中惨不忍睹的证件照,我小表妹百岁的照片,我爸爸年轻时候的军装照,在盒子的最底层放着一张黑白的照片。
姥姥去世有五年多了,这可能会是我这辈子很大的一个遗憾吧。翻遍了家里所有的地方手头上找得出来的就这一张照片,所以显得弥足珍贵。
记忆中,她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女人,并不很漂亮,但是很精神,没有多少文化,却在生活中拿起剪刀,拿起碗筷,下地做活,洗过牛肠,扫过大街。她的生活充满着智慧。她一生养育了6个孩子,把她的岁月,她的一切一切给予了她的儿,孙。
所以说一个女人是伟大的,不光是看到腹部那一道丑陋的疤痕。在那样一个年代,我不知道在毛爷爷所带领新中国的时代是怎样的生活的,每次听姥姥说到高兴的时候,做着女红的时候也能唱起东方红太阳升。从中能感觉到那一辈的人对生活有多么强的热爱。
她矮小的身上游走着岁月,那段饥荒的年代,饱受战争的年代,吃过树皮,吃过草;蝗灾来了吃过土,吃过树根的年代。以及拿起锄头参加人民公社,拎着孩子排队领粮票的场景。
姥姥和我说过,她一生最大的愿望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,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。还有的话就是能识字,读书,多做善事结善缘。
我那时上初中,姥姥每晚看着我写作业,把铅笔用小刀子削的头尖尖的摆在我的铅笔盒里,她经常会指着我的课本问这个字怎么念,或者说那个字长得真好看。
我看着她粗糙苍老的手摸着课本,我递过去笔,她会提议让我教她写她的名字。后来在她的床上,随处能看到她用小刀子裁好手掌大的一沓纸,订书机板板整整齐齐,上面画着一道横,两道横,三道横,四道横,五道横……记着日子。还有她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,像鬼画符一样。
我回过神,打开她去世前长住过的那间卧室,放着很多的杂物,已经没有了她生活过的痕迹。
年轻时代
她1928年1月生人,一到元旦,但凡听到鞭炮就会和我说一遍,她出生的时候是1月1号爆竹声最响亮的时候。
正月十五小区都会放烟花,妈妈说让我和姥姥坐在床边关上灯,看着天空中的烟花。
“姥姥年过去了。”
“恩。”
“姥姥,好看吗?。”
“好看。”
“我怎么觉得一点也没意思。”
以至于以后每年的元旦,十五,我总会想起她。
她的`老家在青岛即墨,住在一个海滨的小山村。老姥姥生了3个孩子,姥姥是大姐,农村里排行老大的孩子总会担负起一些家里的活,所以她从小就要帮着妈妈干农活。
村子里的老人们说,女孩子家不需要读书,姥姥便每天早上早起割草喂猪、喂牛。老姥姥去坡上干农活,在家里的姥姥就要背着小弟弟拉着小妹妹,收拾猪圈牛圈,有的时候还要去放牛。弟弟妹妹长大了一些,要送弟弟去上学,弟弟那时候还太小走不了太远的山路,姥姥就背着弟弟走出去好远一块路。妹妹到了年龄学着做活,但是每次姥姥都让妹妹做些不累的。
当年的生活比现在要困苦许多,没什么好吃的,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肉。每次姥姥的姨母从县城带来些小点心,吃不了的都存好在地窖。那是孩子们最幸福的时光,那个时候孩子们最喜欢过年,那个时候的年最有年味。
老姥姥和姥姥会把鸡蛋煮熟后放进大碗里,守完岁的姥姥的弟弟妹妹就睡去,每次清晨起来,弟弟妹妹口袋里就会有两个鸡蛋。
26岁年龄不小了,邻村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独生子,但是没人愿意去,是因为那家老爷有两个老婆,常年有病,不太好伺候。但他们家的少爷是个有文化的人,姥姥觉得自己没有文化,能嫁给这样的读书人也算是以后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,姥姥在那一年嫁给了比自己小6岁的少爷,也就是我的姥爷。婚后姥爷去县城读书,姥姥就在家里带孩子,照顾三个老人,一直照顾三个老人离世。
心结就是心口那一抹朱红的结痂
那一年,姥姥的了脑血栓,后来的几年我和姥姥睡一张床,睡前经常会一直不停和我聊天,有一次说到自己一共有六个孩子,我用手指数了数发现才五个,我笑她脑袋有些糊涂了。
前年,我给我妈妈买了一身连衣裙,妈妈在镜子面前臭美。
“你身材真好,你们家也就你最苗条了吧,你是不是从小就不爱吃饭?”我坐在沙发一边眯着眼睛望着妈妈。
“从小我确实不太吃饭,小时候你姥姥整天做粗面的窝窝头,吃了嗓子不舒服,我就不吃饭,你姥爷还问我怎么不吃。”
“嘴真挑,还好我不挑,没有遗传你的坏毛病。”我摊摊手,我低玩手机。
“其实,你凤姨是最好看的。”许久妈妈缓缓说出一句话。我抬头见她还在不停看着裙子。
“凤姨?那个我没有见过的姨母?”我一听来了兴趣。
“是呀,她要是还活着估计现在一定是大美女”
“我更是期待她能给我生一个很帅的哥哥,大姨小姨小舅还有你生的都是女的。”
那个姨母叫凤。
当年凤姨才六七岁的样子,像男孩子一样调皮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,姥爷去外地不在家,姥姥去地里干活,中午太阳火辣辣的热,家门口不远,就是一条小池塘,有不少孩子在里面玩。
姥姥干完农活回来,嘱咐其他三个孩子们睡觉不要乱跑,自己也去睡了。凤姨坐在门口,大概是嫌天太热,望着不远处的小池塘的水一圈圈的涟漪。偷偷穿了姥姥的小布鞋跑了出去,近傍晚时分,家门被人敲开,惊醒的姥姥神色慌张的光着脚跑出去,一口气跑到小河边,见凤姨早就没有了呼吸,被一个白衫子盖着,小布鞋没了一个。
姥姥摸着凤姨的小脚,哭了。
那是一个女人最难过,痛心的时候,她一定在自责。
妈妈经常告诉我,一
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,从幼儿园到要去外地上大学,出门前的话一点也没变过,我觉得很是唠叨。有一年我去电影院看了《亲爱的》,故事说的是本来生活如常的一家人,孩子突然失踪了,这一家人一直在不停地寻找,一个家庭牵出了很多这样的家庭。试想想如果孩子真的出了意外,那么那位母亲在以后的一辈子,一定都在自责。
姥姥就是自责了一辈子,即使她还有很多孩子,但是,她始终都会想起那个孩子,那种伤痛是任何一个人都是理解不了的。
她,找了人帮忙把凤姨葬在了祖坟,赶紧找人写了信捎去县城,给读书的姥爷。
远迁离乡
一九八几年的时候,姥爷有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,是去几千里之外的淄博工作,来信让姥姥来淄博找他。
姥姥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小村庄,祖祖辈辈都在这里。可是为了丈夫和孩子的发展,姥姥决定让成人的大儿子留在家里,带着其他四三个孩子去了淄博。
踏出家门的那一刻,她该有多惶恐,一个不识字的女人,千里寻夫。
她来到火车站,不知道怎么买票,在火车站入口,站了好久,怀里的小四,哭闹着,手里的三女儿不敢放手,门口站岗的门卫解放军,走了过来。
“大娘,你这是去哪?”
“俺不识字,要去淄博找丈夫,不知道怎么买票。”
解放军帮着抱着小四,拿着行李,一起去买了票。
“大娘,这孩子有点烫,是不是生病了?”
“哎呦!这可咋办!半天没吃东西了,估计是饿着了。”
“大娘,我带你去我们班长那吧。”
“要钱吗?我没有钱的。”
“不要钱,不要钱你放心。”
在接待站给小四打了针,还吃了些青岛牌子的饼干,那年头饼干是稀罕货。长大之后三女儿也就是我妈妈,嫁给了还是小排长的解放军,我的爸爸,姥姥说解放军踏实,是好人。
因为没有文化,怕丈夫看不上自己,这是她自己和我说的。
她不想呆在家里吃白饭,出去找了一个扫马路的工作。每天六点上班,晚上六点回来,准备饭招呼孩子们吃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
这样一个勤快的女人,看着大女儿结婚,二女儿结婚,三女儿结婚,小儿子结婚,有了第一个外孙子,外孙女,孙女慢慢的,步入了老年。
饱受病痛的折磨
2004年的时候她患上了脑血栓住进了医院,而后长达很久的时光里,她的左边不协调,腿不利索,手不能我成拳头。
我爸爸常年在外当兵,所以妈妈把姥姥接到家里。但是住在家里一天也不闲着,趁孩子们睡着的时候,拿起他们的鞋子,纳鞋垫,一个又一个,说以后可以留个念想。孩子们去上班,自己一个人在家里,有时拄着拐杖出去把被子拿出去晒,不忘用拐杖打一打。
我的成绩一直不是很优秀,但是每次被说教的时候,我就会跑到她身边诉苦,她就觉得自己的外孙女最好,和社区里的老太太们聊天的时候也会很骄傲的说自己的孩子,这个还那个好,给她买这个买那个。
人老了有的时候行动迟缓,可能会有种没用的感觉,被自己的孩子说几句就会,自己闷闷在房间里一下午。有的时候会自己偷偷抹泪,我们不能体会她那种痛楚,是来自衰老迟暮的难过。
我小学的时候学习一段时间的二胡,姥姥鼓励我,说我有一个舅老爷小时候学习小提琴,拉的很好是家里的骄傲,不过英年早逝了。但是她一直说那先过往。
我上高中后,她回到了自己家,我也忙着自己的学业,很少去探望她了。但是每次去都会教我们怎样坐板凳不会摔倒,怎样喝粥不会烫着,过年口袋里都会有两个鸡蛋碰在一起脆着声响,还有叫我名字时候清还有洪亮的大嗓门,缝鞋垫时唱着东方红。
思念是最长的祭奠
我不知道“思念”这两个字是谁发明出来的,在我想不出任何语言表达感情的时候用,最贴切。
每年正月十五放烟花的时候,我把灯关上,在黑暗笼罩的卧室,看得见远处烟花起起落落,默默坐在窗前,就一会。
小时候,太无知,不懂得去珍惜。不知道去多拍几张照片,多去陪陪她,多留下些和她的记忆。
2011年4月28号,劳动节前,那天阳光很好,不冷不热。
下了晚自习去姥爷家吃饭,我当时物理测试没有及格,很不开心,坐在床上哭,姥姥在一边安慰我,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鸡蛋塞进我手里。
马上上晚自习了,我走前拉着她的手说。
“姥姥。后天放五一我来看你。”
晚自习回家后因为一点小事情,我和妈妈吵了架,那晚胸口很闷,闷得睡得不好。
然后29号凌晨姥姥就走了。
在那个黑色的星期五。
我脱下了花花绿绿,披上了刺眼的白衣。
在殡仪馆,妈妈哭昏过去了。
后来姥姥的妹妹着儿子闻讯带从老家赶来。当晚供桌上放着的长明灯,烛火婆娑,坐在客厅姨姥姥擦着姥姥的遗像。
多年不见,再见离别。
“姐,你怎么走了呢……”
在哭声中,我终于知道别人有,我没有是什么感觉了。为什么亲情这么容易就溜走了呢?
猝不及防,以至于我哭得这么狼狈。
现在有时,妈妈会和我说,她很想姥姥。我也很想但是我从来没说过,有时做梦也会梦到,醒了之后,就自己念叨念叨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每次走到单元门口,老是会感觉家门就已经被打开,她叫着我的名字站在门口迎着我;走进姥爷家那条小巷,总觉得拐进胡同,就会看见她拄着拐杖走出来向我微笑。
路过幼儿园的时候,看着大门里的秋千随着风晃来晃去。那是年幼的我被姥姥推着荡秋千,我回过头对姥姥说。
“姥姥,你等我以后长大了,给你买个大房子,然后咱们搬进去,买只花猫。”
叶欲停而风不止,子欲孝而亲不待。
这个愿望,永远实现不了了。
我知道,思念的时间还会很长,我只能不停地,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,放肆的哭,放肆的去回忆她,然后让回忆结痂慢慢变成岁月的一部分。
我还记得,姥姥离开的那晚,凌晨下起了冰雹,打坏了小区门口的路灯,打落了很多的树枝。
但是,那一夜的雨再大,也冲刷不了我的思念。
那一夜的风再大,也吹不尽我的泪水。
第二天,早早起来去姥爷家帮忙料理后事,踏着脚下的树叶很是厚重,如同我那时沉重的心情。
如果我还有机会
,那么我会用行动去陪伴,而不是用文字去纪念。慢慢地成长付出的代价就是,理解那些原来没有想明白的道理,失去在身边看似不重要的东西,慢慢多了许多的遗憾,在遗憾中去回味时光留下的苦涩,也是在遗憾中明白什么是幸福。
泰戈尔说过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的距离。是鱼与飞鸟的距离。
对我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是无法跨越生死,无法说一句我很爱你,我很想你。
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些动人的字眼,我不知道在小时候为什么要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。那个夏天是悲伤的夏天,因为我失去了再也无法挽回的东西。
在向而立之年的路上迈进的我,开始学会了珍惜,留意身边的重要的人。妈妈对我说什么时候学会珍惜都不算晚。
有本书的结尾,说了一句很诗意的话:
太思念一个人的话,那个人就会穿越生死来到我们的世界,我们的记忆会遗落在某处,变成一朵花,一把伞,一条鱼,一道彩虹,或者是一块碎片。
等待着我去触碰,将它们唤醒,然后我们重逢。
此文奠第五个年头故去的她。
以此共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