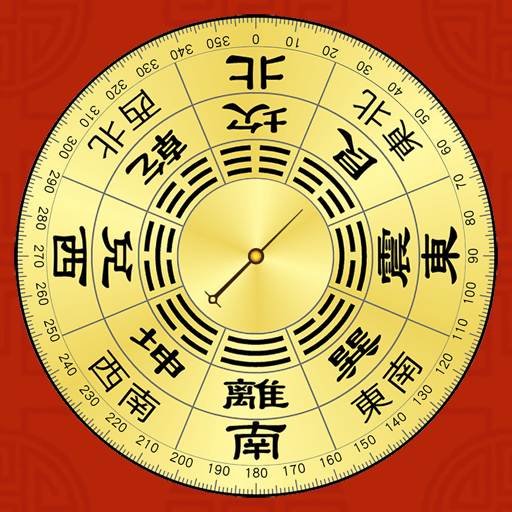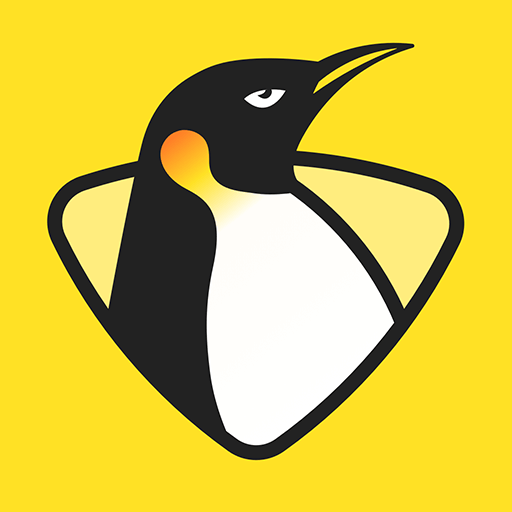《东坡志林》里有篇文章,题目叫《司马迁二大罪》。文章开头写道:
商鞅用于秦,变法定令,行之十年,秦民大悦,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,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。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,诸侯毕贺。苏子曰: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,而司马迁闇于大道,取以为史。
商鞅变法牛,厉害,上到天子,下到草根,都服。且慢这一切在苏轼这里都成了吹牛皮,没有的事儿,全是战国游士的“邪说诡论”。可惜苏轼并没有给出得出此结论的证据和论证过程。
《史记》,了不起,伟大。但再伟大也有错误的地方。司马迁是人不是神,他所能见到的材料也有限,有些今天能看到的在他之前的古人的东西,他看不到;今天的考古学,那时没有;C-14等手段,连想象也不敢。虽然他也拼了老命,做到一分证据说一分话。
苏东坡不讲这些,一句“闇于大道”的大帽子,足够了。
苏轼继续写道:
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,其先黄、老,后《六经》,退处士,进奸雄,盖其小小者耳。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、桑弘羊之功也。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、桑弘羊,而世主独甘心焉,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,甚者则名实皆宗之,庶几其成功,此则司马迁之罪也。
所谓的“先黄老,后六经”,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。在儒家的信奉者们看来,圣人的六经才是最大的真理。做什么事必须把这面旗帜高高举在最前面最高处才行,断不能放在次要位置。“盖其小小者”,是相比于下面将要说的“大罪”而言的,但不是没问题,问题是政治不正确。
读《孔子世家》,不难发现,司马迁对孔子是怀有极大敬意的。但就像有人尊敬释迦牟尼,并不一定就会剃头当和尚一样,司马迁并不是儒家的孝子贤孙。他的父亲司马谈“学天官于唐都,受易于杨何,习道论于黄子”,而他继述其父所学之外,又从董仲舒学《春秋》,从孔安国学《古文尚书》。他是一个综核百家,学究天人,自成一家的人物。如果一定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,我觉得道家更适合他。司马迁郑重记录的《六家要旨》一文,对阴阳、名、儒、法、墨五家的每一家,都是有褒有贬,唯独对道家都是肯定的话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,可以称之为“法自然”的思想,这也是属于道家的观念。读《平准书》、《货殖列传》,自然明白。
你可以骂道士不把佛经放在道经前面吗?
我可以骂司马迁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吗?
可以当然可以,而且必须可以。
班固、苏东坡就是这样的神逻辑。
更神的是苏东坡认为“论商鞅、桑弘羊之功”是司马迁的二大罪恶。
真不知道苏东坡怎么读的《史记》。在司马迁笔下,所谓的商鞅之功,只是司马迁所做的客观性描述,而他对于商鞅的“刻薄寡恩”,是从内心非常反感的。桑弘羊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还活着,不可能给他作传,除非他是汉武帝。对于所谓的桑弘羊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之“功”,主要记载在《平准书》里。但是那根本是司马迁对汉武帝、桑弘羊们与民争利、算入秋毫的声讨书啊。
“不隐恶,不虚美”,秉笔直书,有么说么,这是司马迁著史的原则。他可以讨厌商鞅、桑弘羊们,他也不隐瞒对他们的讨厌,可对于他们的事实,所谓的“功”,也不会装作看不见。
在苏轼这里怎么成了罪状了?
中国历来有个不好的传统:对好人,变着法地说好,造神,完美化;对坏蛋,脏水可劲地泼,弄臭,妖魔化。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蛋,也没个准谱。今天香明天臭,河东河西,风水轮流转。
这种路子现在还大行其道。
一定要司马迁只说商鞅、桑弘羊们的罪恶,而不说他们的“功”,才对?
苏轼就是这样想的。在他看来司马迁论了他们的“功”,使后来的世主有样学样,都变坏了,这个责任就是你司马迁的。
殷纣王表示不服。
周厉王强烈反对。
苏轼继续论述:
秦固天下之强国,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,修其政刑十年,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,虽微商鞅,有不富强乎?秦之所以富强者,孝公务本力穑之效,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。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,如豺虎毒药,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,则鞅实使之。
秦国富强和商鞅无关?
那在《上神宗皇帝书中》,怎么说“惟商鞅变法,不顾人心,虽能骤至富强,亦以召怨天下”呢?
没关吗?还是作《上神宗皇帝书》的苏轼是个假苏轼?
富强没商鞅的份,而“子孙无遗种”的锅,却要商鞅背。
贾谊气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:写什么《过秦论》,白费劲了!
说完老商说老桑,苏轼又写道:
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,穿窬之智,无足言者,而迁称之,曰:“不加赋而上用足。”善乎!司马光之言也,曰:“天下安有此理?天地所生财货百物,止有此数,不在民则在官,譬如雨泽,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,不过设法侵夺民利,其害甚于加赋也。”
误解司马迁请出司马光,让他给自己站台,老苏要放大招了。
司马光的《迩英奏对》,写自己和王安石辩论。针对王安石的“善理财者,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的观点,他说:
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,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,止有此数,不在民间,则在公家,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,不取于民,将焉取之?果如所言,武帝末年,安得群盗蜂起,遣绣衣使者逐捕之乎?非民疲极而为盗耶?此言岂可据以为实。
用此司马反对彼司马,有趣。只是司马光认为司马迁是讥讽汉武帝,而苏轼认为不是,是的话那就不是司马迁的大罪了。
所以因此是以,必须,不是。
苏文以下内容和司马迁没关系了,不说。
王安石有《商鞅》诗:
自古驱民在信诚,一言为重百金轻。
今人未可非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
“凡是敌人反对的,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,我们就要反对!”商鞅、桑弘羊必须被骂。没办法历年来都按这么个套路来玩的。
骂他俩就可以了,怎么还把账算到司马迁头上呢?聪明如苏学士,真看不懂《史记》?
东坡先生啊你这是弄得个啥!